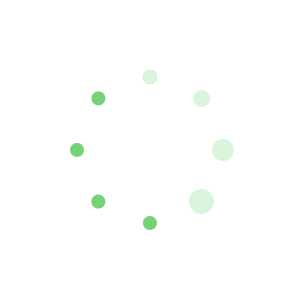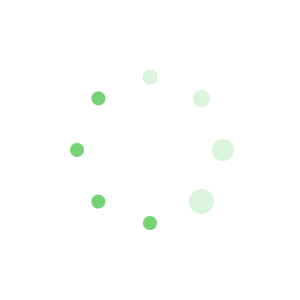小说和散文区别要点(精选2篇)
1.小说和散文区别要点 篇一
孤单和孤独的区别散文
世事无常,人过时迁。世上的人事不可能永久保存,正如李白所说:“人生在世不称意。”所以我们活在这世上,就应该乐观一些,不能悲观,悲观的话,注定输掉这一生。尽管世态炎凉,但我们还是能做好自己的,既然能做好自己,那就做最好的自己。其实现在的世界,多数人喜欢帮自己穿上一层保护膜,也就是把自己伪装起来,就像变色龙一样,把自己伪装起来,不愿在外人面前表现真正的自己,可是这样的话,你对他伪装;她对你伪装;他又对她伪装,这样又有什么意思呢?我们是否曾经扪心自问:我是否拿心交友,还是甘愿做狗?真心对待他人,才能换来他人的`真诚对待。只有这样我们身边才会有更多的缘,而不是怨。缘与怨,读起来一模一样,可两字的意思确实天壤之别,你若想得到他人的缘,需将心比心;你若要为了保护自己而伤他人,换来的只是怨,当然,这也要看你自己的意愿啦。你自己若是不愿,即使他人掏心掏肺亦是徒劳。
每个人一生都会有不同的经历,都会遇到丝丝情感、种种羁绊,但我们该如何处理?处理不当的话,会让我们手忙脚乱,感情亦会变得交错复杂;处理得当的话,则恰恰相反,处理得当就会有条有理,感情亦会有序简单。我们也要经历生老病死,也会有乐、有悲、有愁、有伤、有泪、有苦、有甜、有孤独、有难过、又寂寞……可以说我们的人生是多姿多彩的,只不过有些人命好,乐多一点;也可能有些人命不好,愁多一些,可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样我们都不知道,一切都取决于我们自己怎样去面对。微笑去面对,将会出现一片广阔无垠格外晴朗的天空;哀伤面对,出现的将是狂风骤雨格外凶狠的天空……
2.小说和散文区别要点 篇二
关键词:历史叙事;历史小说;真实性
中图分类号:K01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6.06.0043
从叙述主义(Narrativism)的角度看,叙事(Narratio)是史学和小说共有的表现形式,所以“如何在历史叙事和历史小说之间划界”是叙述主义历史哲学首先要面临的问题。一直以来,人们认为历史叙事是真实的,而历史小说则是不真实的,甚至是虚构的。这一说法现在看来显然是站不脚的,有学者就指出:“讨论当代历史小说,‘真实是肯定绕不过去的一个话题。”[1]71换言之,历史小说也要追求真实。所以,“真实性”标准对此无效。如此看来,如何区分二者依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难题,而如果无法从理论上辨析出二者的区别,那么叙述主义的理论框架也就无从建立。再者,从国内外历史哲学研究的现状看,叙述主义都是一门显学,不过,在这些汗牛充栋的文献中,对这一最基本问题具有启发性的探讨则寥若晨星。基于此,重新思考这一问题就很有必要性。
一、安克施密特的叙述主义观点
安克施密特(F.R.Ankersmit)是叙述主义历史哲学的重要创始人之一,他的观点极具代表性和启发性,以他的理论作为分析的起点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众所周知,叙事作为一个文本,从整体看,它是一组话语;而分析其成分,该话语则由一个一个的陈述句子所构成。所以从叙述主义的观点看,每一个叙事内在地都包含着两个层次,“一个较低的层次——即关于特定事件和情境的事实陈述,以及关于特定历史时期之性质的总体评价层次。”[2]24前者指的是叙事所包含的单个陈述句子,后者指的是由这些单个的陈述句子所构成的那个融贯一致的总体——这也是后来安克施密特所说的叙述实体(Narrative Substance)。前者也可以称之为叙事的微观层面,后者则是宏观层面。比如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这一著作,从微观层面看,它包含着大量的关于法国大革命的陈述句子;从宏观层面看,该著作则呈现出一幕悲剧;而单独从微观层面看,我们无法洞悉该著作的悲剧性,悲剧性是该著作在整体上所呈现出来的特征。所以,安克施密特的这一划分有其合理性。
与此相对应,安克施密特认为历史叙事和历史小说区别有两点:第一,从目的来看,历史叙事是为了获取对历史的总体性评价这一知识,即那个由诸多单个历史陈述构成的总体,也就是文本的宏观层面;而历史小说则是应用这一知识。换言之,历史叙事相当于理论科学,历史小说则相当于应用科学,前者生产历史知识,后者则应用历史知识[2]24-25。比如我们可以说,《旧制度与大革命》这部历史叙事中所包含的陈述句子是为了获取这一对法国大革命的总体性评价——即法国大革命仅仅是一出令人唏嘘不已的悲剧而已。另外,狄更斯描写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小说《双城记》中批判革命大众盲目屠杀,在憎恨贵族社会对他们残酷压迫的同时,自己也变成了一种畸形的社会阶层,除了仇恨和报复,一无所获,这也充满了悲剧色彩,所以可以看作是对《旧制度与大革命》所阐释出来的关于法国大革命总体性评价观点的应用。
第二,从叙事两个层面之间的逻辑关系看,在历史叙事中,微观层次会导向宏观层次:即前者为后者提供证据和论证;而在历史小说中,情况正好相反,历史小说家先有总体性评价知识,然后把该知识具体化为特殊的、个别的事件[2]25。也就是说,历史小说总是先入为主,戴着有色眼镜看历史;而历史叙事则不能如此,因为“‘观点在历史讨论中是重要的问题:人们不是从它们出发去论证,而是为它们作论证。”[3]27换言之,在历史叙事中,其逻辑进路是由微观导向宏观,而在历史小说中则是由宏观走向微观,比如我们可以说,《旧制度与大革命》是运用一系列的陈述句子来证明大革命只不过一出悲剧;而《双城记》则先有这样一个看法即大革命是一出悲剧,然后虚构一个故事来表现这一点。
当然,这两个区别是一脉相承的,正因为它们的目的不同,所以它们的行文逻辑进路也不同。
二、对安克施密特叙述主义观点的反思
现在来看看安克施密特的观点是否经得起推敲。先看第一个区别,即历史叙事的目的是获取历史知识,而历史小说则应用历史知识。这个说法是经不起推敲的。首先,历史叙事也不见得全部是在获取历史知识,它也可以去论证已经存在的历史知识的正确性,比如关于阶级斗争史观,就有大量的反反复复的历史叙事在应用它,而不是创造新的历史知识。其次,历史小说也不见得只是应用历史知识。亚里士多德曾说过“诗歌比历史更真实”,那么历史小说是否有时候也会比历史更真实呢?这个可能性当然是存在的,比如《双城记》就很难说它只是在应用《旧制度与大革命》所获取的知识,倒不如说它也在获取历史知识;再如中国以《红高粱》为滥觞的所谓“新历史小说”,就是对俗称的“十七年”传统小说的反叛,如“《红高粱》与以往革命历史小说的不同在于……作品淡化了宏观、规范的意识形态言说,将国共两党的抗日力量推到幕后,确立了一种以民间历史观和野史为核心的历史叙述方法。……此类作品在20 世纪末期蔚然成风,它们为读者提供了解读历史的别一路径。”[4]
历史小说可以通过虚构的特殊的人物的故事来“证明”作者对这段历史的独特的理解,这就是在获取历史知识。从理论上看,可以说无论是历史叙事还是历史小说,都是理解历史的方式,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来获取历史知识,而不能如安克施密特那样先入为主地把历史小说定位为仅仅是应用历史知识。这只是两种不同的知识而已,历史叙事主要依靠理智和逻辑的力量来获取知识,就如安克施密特所认为的历史叙事的话语是解释性和论辩性的[3]25,而历史小说则依赖直觉、体验、同情等方式来获取知识。从逻辑的角度看,历史小说所表达的观点其有效性是非常有限的,经不起逻辑的拷问。所以,无论从史学实践看,还是从理论上分析,历史小说也可以以获取知识为其目的,而不仅仅是应用知识。
综合起来看,无论是历史叙事还是历史小说,其目的既可以是获取历史知识,也可以是应用历史知识。与此相对应,它们二者的逻辑进路也是如此,既可以从微观走向宏观,反之亦可,当其是在创造历史知识时,它的逻辑进路是从微观导向宏观;当它是在应用历史知识时,则相反。从另外一个角度看,逻辑进路是作者在创作之初或者创作过程中会遇到的问题,是作者对叙事的原初规划与设计,好比建房子先要有整体规划、有图纸,创作叙事也得先有整体规划,这一整体规划就是指导着创作的具体逻辑进程,在此是先有宏观,后有微观,这对于历史叙事和历史小说都是如此。而在实际的创作过程中,具体的行文顺序确实是从微观到宏观,就好比建房子,要一块一块砖砌起来才能建成大厦这一整体,从这点看,逻辑进路又是从微观导向宏观,这对历史叙事和历史小说来说也是一样的。
退一步讲,即便我们认同安克施密特的这个说法,这也无法成为区分二者的有效性标准。如前所述,诸如创作的目的以及与此相一致的叙事的逻辑进路之类的问题,都是作者在创作之初的规划,存在于作者的意识中,而不是存在于叙事文本中,也就是说,单纯地分析某个叙事文本,我们无法看出它是在获取历史知识还是在应用历史知识——我们只知道叙事蕴含着历史知识,但我们不知道该知识是作者原创的呢还是他从其他地方借用过来的,也无法看出其逻辑进路究竟为何——我们只知道在叙事中微观层面和宏观层面是有机地融为一体的;准确地说,这些问题是作者在创作叙事的过程中出现的,是在创作过程中需要解决的问题,当创作完成了,一部完整的叙事出现的时候,这些问题也就烟消云散了,它们在叙事中也不会留下痕迹。所以,单纯分析叙事文本根本看不出谁先谁后,这就好比建房子,建房的顺序确实是先一楼后二楼以此类推,但是房子建好之后,我既可以从一楼走上顶楼,也可以从顶楼走下一楼,都很顺畅,同样的道理,一个完整的叙事,从微观入手可以导出宏观,从宏观开始也可以理解微观,逻辑上都是顺畅的,这对于历史叙事和历史小说也是一样的。显然地,诉诸于逻辑进路还是无法区分历史叙事和历史小说。
按照这样的分析,不难看出,作为叙述主义代表的安克施密特所提出的区分历史叙事与历史小说的标准已经超越了叙述主义本身,换言之,他无法在叙述主义论域之内找到合适的标准,这是叙述主义的局限,还是安克施密特的局限?所以,总起来看,安克施密特对历史叙事和历史小说的划界是不成功的,还得另辟蹊径。
三、一个改进性的理论:之一
如前所述,安克施密特认为叙事内在地包含着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本文认为这种分法依然过于粗糙,宜把它分为三个层面——微观、中观和宏观,微观和宏观与安克施密特的是一样的,所谓中观指的是叙事的深层结构即其语义核心——这是不带细节的小故事[3]63,具体而言,该结构指的是以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这几个要素支撑起来的叙述框架,该框架是以陈述句子为基本要素,依照历史的逻辑前后衔接在一起所构成,它是这样的形式——“如果你有一组大意为A的句子,这组句子后面必须跟着一组大意为B的句子,它的前面必须有另一组大意为C的句子,等等。”[3]63依照这样的思路,我们就区分了叙事的三个层面:其一,微观层面——它指的是叙事所包含的一套单个陈述句子,其功能有二,一是为建构中观叙事提供素材,二是在中观叙事的框架之内展开历史的细节,让叙事生动丰满起来;其二,中观层面——叙事的语义核心,决定着叙事的内在逻辑进程;其三,宏观层面——代表叙事的整体,是叙事主旨思想的体现,表达了对历史的一种独特的理解。
安克施密特曾说过,历史叙事和历史小说二者的区别是微观和宏观之间的逻辑关系不同,依照我们对叙事的三个层次的划分,其不同的逻辑关系就不是存在于微观和宏观之间,而应该是存在于中观层面和宏观层面之间,因为很显然的,微观层面指的是散乱的、无意义的陈述句子,是建构叙事的原始素材,这是一种被动的、消极的存在,这个层面自身的意义是空的,因此它不可能和宏观层面之间存在逻辑关系。这种逻辑关系只能存在于中观和宏观之间。
那么,历史叙事和历史小说各自的中观层面和宏观层面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呢?对应于两种不同的知识,也有两种不同的关系。本文认为,在历史叙事中,中观层面和宏观层面之间的关系应该是蕴涵式的;而在历史小说中则是表现式的。所谓蕴涵式关系,指的是宏观和中观之间的一种推理关系,具有较强的逻辑说服力,从而对历史提供了一种合理的让人信服的解释,这和海登·怀特所说的形式论证式解释有类似之处,他说:“这种论证可以分解成一个三段论:包括一些推定的因果关系普遍规律的大前提、规律适用于其中的涉及边界条件的小前提,以及结论,即实际发生的事件都是根据逻辑必然性由上述前提推导而来。”[5]12换言之,宏观和中观之间是一种逻辑蕴涵关系,而且这个逻辑方向是双向的,既可以从宏观到微观,也可以相反。不过和海登·怀特不同的地方在于,他说“我称之为形式的、外在的或推理的论证式解释。”[5]12这就是说,在怀特看来,这种逻辑关系是外在的,这是本文所不能同意的,如果是外在的,那么历史学家就可以随意地建立此类关系,这显然和史学实践不一致,所以本文坚称这种关系内在地存在于宏观和中观之间。
那么什么是“表现式关系”呢?这里面的关键词是“表现”,对应的英文为“Representation”安克施密特对此有专门研究,他指出,“‘表现的词根可以让我们接近其本体论属性:我们通过展示某一不在场者的替代物令其-再度呈现(re-present)。原本的事物不在了,或者为我们所无法触及,另外之物被给出以替代它。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这样说,我们用史学补偿本身不在场的过去。”[6]依照这样的观点,历史小说是某一不在场的替代物,那么这个不在场的东西是什么呢?对于历史叙事而言是历史实在;对于历史小说而言,则应该是作者对历史的理解,换言之,这一不在场的东西是作者的思想,是观念实在,所以历史小说是作者思想的替代物或语言呈现。
所以相对于逻辑的、推理的关系而言的,表现式关系,只是把作者的主旨思想通过语言形式再现、叙述出来,使其得以成型、到场,但它不对这种思想给出论证,这一点和海登·怀特所说的“情节化解释”是一致的,他说,“情节化是一种方式,通过它,形成故事的事件序列逐渐展现为某一特定类型的故事。”[5]8叙事就是情节的集合①,历史小说都是通过某个或某些虚构的特殊人物的故事——即特殊的情节——来再现主旨思想的,而从逻辑的角度看,这些故事情节当然不足以“证明”该主旨思想,而只能是表现该思想而已,好比狄更斯的《双城记》,该小说所叙述的故事只是表现了而非论证了狄更斯对法国大革命的理解。
四、一个改进性的理论:之二
如上所述,历史叙事和历史小说的区别就在于中观层面和宏观层面逻辑关系的不同,前者是蕴涵式的,后者是表现式的。但这是否就是令人满意的标准了呢?设想一位历史小说家撰写了一部推理小说,逻辑非常严密,可谓是严格的蕴涵式的,那它难道就是历史叙事了吗?对此,或许传统的真之标准并非如安克施密特所言是可以抛弃的,确实,单凭“真”这一标准无法区分历史叙事和历史小说,因为对于历史小说来说,真不是一个本质要素,历史小说可以真,也可以假;而对于历史叙事来说,则一定要真,这是它的一个本质要素。既然如此,那么我们至少可以凭借“真”这一标准来证伪一部历史叙事,即假如某个作品不真,那么它就不能成为历史叙事家族的成员。对此,安克施密特的这一倾向是值得警惕的,他说,“由于对历史文献的不准确的阅读,历史学家的叙事也可能包含假陈述……”[3]22他似乎倾向于说历史叙事也可以虚构陈述,对此彭刚也对安克施密特提出了类似的批判,他说,“对于历史叙事整体而论,是否可以如安克斯密特所言,将真假完全摈弃在其衡量标准之外呢?……从这些角度看,认识论问题虽然未必能够穷尽历史叙事层面所出现的问题,或者甚至不是这一层面的主要问题,但却也不是轻易就可以驱逐出去的。”[7]看来“真”对于历史学来说确实是无法抛弃的,这是原则问题,就好比不能因为某些官员贪腐而推导出官员可以贪腐这一结论一样,也不能因为某些历史叙事包含有假陈述而推导出历史叙事可以虚构陈述。据此可以发现,诚如多米尼克·拉卡普拉 ( Dominick LaCapra)指出的那样,在历史叙述中也应该为批判理论保留一席之地[8]。
那么,历史学之“真”存在于哪一个层面呢?首先,作为总体性评价的宏观层面,它应当为真。而对于微观层面,则应一分为二来看,对于那些构成叙事语义核心的陈述来说,一定要真实;对于那些叙述细节来说,则可以虚构,即在真实的叙事深层结构之内来虚构——这应该是历史学虚构的合理性所在。而中观层面,即叙事的核心语义结构,这也应当真实,其真实性含义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形式上的真,即构成该结构的陈述句子应该是真的,二是实质上的真,即这些陈述句子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是真的,和历史的逻辑相一致。所以,这样看来,历史学之“真”主要就体现在宏观和中观层面上,这是一定要真实的。但有一点值得强调,尽管叙述的细节可以虚构,但它有个限度即以历史学研究为基础,当该研究可以提供相关细节时,就不要虚构,当不能提供时,则可以虚构,这是一个动态的真实。在这一点上,历史叙事是可以被证伪的,所以它对“真、假”的批判持开放态度,而历史小说则不具备这一特征。
那么,对于历史小说而言,同样地在宏观层面应当真实,在微观层面则完全可以虚构,而中观层面也可以虚构,只不过这个虚构应该具有合理性,即“作品中情节的发生、发展和终结,必须为所处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社会条件所允许;作品中人物的性格、命运,他们的追求、他们的生活逻辑,也应该是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的产物。”[9]无疑这是一个抽象的标准,但它确实存在。
这样看来,关于真实性,历史叙事和历史小说的共同点在于,宏观层面都应当真实,其区别在于两点:其一在中观层面历史叙事应当真实,而历史小说则不一定;其二在微观层面历史叙事追求动态的真实,而历史小说则完全可以虚构。
五、结 语
所以总起来看,我们就有了两条区分历史叙事和历史小说的标准:一是看其中观层面与宏观层面之间的关系,二是考究叙事中观层面的真值。如果某个叙事其中观和宏观层面之间的关系是蕴涵式的,其中观层面的核心语义结构又是真实的,那么,我们就可以大体确定该叙事是历史叙事了。如果不能满足其中的一条,那么就可以说它是历史小说②。
但我们会发现即便这样,还是存在模糊之处。如果一部公认的历史小说也满足了这两点,那么它还是历史小说吗?从本文的逻辑看,像这样的历史小说,称之为历史叙事也无妨,这鲜明地表明了历史叙事和历史小说二者关系之密切,而且它们之间存在交集——即有些叙事既可以说是历史小说也可以说是历史叙事。之所以如此,从理论上分析,我们所提出的两条相对比较有效的区分的标准,都不是严格的,这两条标准对于历史叙事来说是充分必要条件,但是对于历史小说来说则既非充分也非必要条件,换言之它们可以满足这两条标准,也可以不满足,可以满足其中一条,也可以一条都不满足,这是导致它们出现交集的理论原因。而从史学实践看,也确实有大量的叙事身份暧昧,比如《马丁·盖尔归来》这部著作,就既可以是历史叙事也可以是历史小说,这是以叙述主义为代表的后现代历史哲学可以把历史叙事美学化的理论原因所在,也是在后现代语境下历史学和文学趋同的理论根源。
注释:
①当然,历史叙事也有情节,但它和历史小说的情节是不一样的,前者具有某种“现成性”。
②在此,读者可能会质疑说,不是历史叙事就一定是历史小说吗?不可是其他类型的吗,如诗歌、戏剧、散文等?对于这一质疑,我想说,本文的主旨就是比较历史叙事与历史小说,而且根据安克施密特的观点,历史小说和历史叙事二者是最相似的,也是最难区分的,所以本文隐含的语境是这样的,即一部合格的叙事,不是历史叙事就是历史小说。而如果某部叙事不是历史小说而是其他的艺术形式,那这个问题根本就不存在。
[参考文献]
[1]蔡爱国.论当代历史小说真实性的维度[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3):71-76.
[2]Frank Ankersmi.Narrative Logic:A Semantic Analysis Of the Historians Language[M].Hague: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1983.
[3]安克施密特.叙述逻辑:历史学家语言的语义分析[M]. 田平原,译. 北京:北京出版社,2012.
[4]张冬梅,胡玉伟.历史叙述的重组与拓展:对新历史小说与“十七年”历史小说的一种比较诠释[J].当代文坛,2003(2):19-22.
[5]怀特.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M]. 陈新,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
[6]F. R. Ankersmit. 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M].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11.
[7]彭刚.从“叙事实体”到“历史经验”:由安克斯密特看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的新趋向[J].历史研究,2009(1):155-173,192.
[8]Dominick LaCapra. Historical and Literary Approaches to the “Final Solution”:Saul Friedlander and Jonathan Littll[J]. History and Theory, 2011(50):71-97.
[9]金元浦.文学解释学[M ].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136.
(责任编辑 文 格)
Abstract:Ankersmits answer to wha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historical narration and historical novel cannot be satisfactory. Every narration contains three logical levels: the micro, the middle and the macro. Therefore two differences between historical narration and historical novel are as follows: one is the logical relation existing respectively among their three levels, the other is their respective demand of “truth”. Furthermore, there is still an overlap between them which is the reason why narrativism could aestheticize historical narration and why the historiography and the literature go to converge.
【小说和散文区别要点】推荐阅读:
记叙文和散文的区别04-11
散文复习要点06-24
父亲和桃树散文09-28
梨花少年和母亲散文10-28
我和梨花约会散文12-23
散文好句子和感言03-25
喜欢和爱的散文07-23
流星和萤火虫散文12-13
品味音乐和人生优美散文02-16
理想不能和现实做交易散文1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