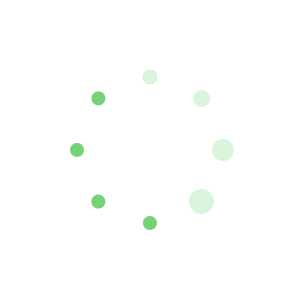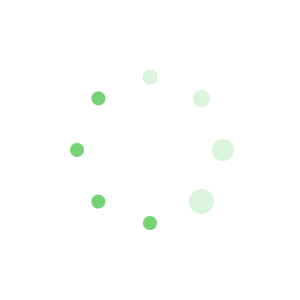死亡病程的书写范文(精选3篇)
1.死亡病程的书写范文 篇一
死亡记录和死亡病例讨论记录的书写要求
1.死亡记录
病人住院期间因救治无效死亡者,应在死亡后立即完成死亡记录,由经治医师用红墨水笔书写在“死亡记录”专用单上。其内容与出院记录大致相同,但必须着重记述抢救亡情况,其内容包括:
(1)一般项目:姓名、性别、年龄、入院科别、死亡科别、床号、门诊号、住院号、入院时间、死亡时间(注明时、分)、住院天数、入院诊断、死亡诊断、记录时间(注明时、分)。
(2)入院病历摘要。(3)住院经过摘要。(4)抢救经过。
(5)最后诊断及死亡原因。
(6)对死亡病例不论诊断明确与否,应努力说服死者家属,作尸体病理解剖,并将尸体检
查结果纳入病历中存档。
2.死亡病例讨论记录
凡住院死亡病例应在1周内由科室组织死亡病例讨论,医护和有关人员参加,分析死亡原因,吸取诊断治疗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并用蓝黑墨水笔分别记入病历(另立专页,在横行适中位置标明“死亡病例讨论记录”)和死亡病例讨论记录本中。其内容包括:(1)讨论时间、地点,主持人、参加者的姓名、职务(职称)。
(2)病人姓名、科别、年龄、入院时间、死亡时间、死亡原因、最后诊断(包括尸检 和病理诊断)。
(3)参加人员发言纪要。(4)主持人的总结意见。
死亡患者的门诊病历附在住院病历后一并归档。
2.死亡病程的书写范文 篇二
一
《日光流年》讲述的是一个反抗命运和自我救赎的故事。耙耧山脉的深皱之间地人烟稀少, 水土两旺, 于是杜、蓝、司马三姓搭棚而居, 通婚繁衍, 人畜两盛。然“百余年来, 三姓村人又大都死于喉堵症, 人的寿限从六十岁减至五十岁, 又从五十岁减至四十岁, 终于就到了人人都活不过四十岁的境地”。为了战胜死亡, 三姓村开始与命运抗争, 村中每任村长均以带领全村人活过四十岁为任。杜拐子教导村民多生育, 使出生率高于死亡率以此来保障族人不致消亡;司马笑笑推广种油菜, 以期能终止宿命;蓝百岁认为只要把全村的田地翻新就能产出新的粮食, 从而摆脱厄运;第四任村长司马蓝从少年时就渴望能当上村长以引来“灵隐水”, 让村民跨越四十岁的大限。然而一切均以失败而告终, 无论是多生孩子、广种油菜还是翻土, 都没能改变命运, 司马蓝的灵隐渠虽然已经挖通, 引来的却不是传说中灵隐寺的“灵水”, 而是外面世界的臭水。
《日光流年》的扉页题辞是:“谨以此献给给我以存活的人类、世界和土地, 并以此作为我终将离开人类、世界和土地的一部遗言。”可见阎连科对这个世界的眷恋。这也正合了他在那场谈话中讲的:“无论写什么, 我的作品都离不开土地, 都是土地之花, 哪怕是‘恶之花’”。这种传统的乡土观念构成了阎连科小说的精神资源之一。
其小说的另一精神资源是基督教信仰。《日光流年》五卷救赎故事中, 第四卷无疑是极为引人注目的。这一卷共十三章的章首都引用了《圣经》上的话作为引子, 第三十四章引用《圣经·出埃及记》神召唤摩西的经文, 所对应的, 是蝗灾要来时村长司马笑笑号召村人保住油菜, 不要保秋粮, 因为吃油菜才能活过四十岁。第四十一章引用《圣经·民数记》神赐鹌鹑为食物的经文, 对应的是村人捕捉吃了村里残孩死尸的乌鸦作为食物。而第四十六章写到“果然获得了那宽阔的流奶与蜜之地”, 也是借用圣经中上帝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来到流奶与蜜的迦南美地的典故, 但这句话并不出于《圣经》, 乃是阎连科自己所写。只是, 以色列人在上帝的带领和指引下, 最后走到了迦南地, 而三姓村的人自我救赎则宣告失败了。这样的书写究竟是对上帝带领的歌颂, 还是对自我救赎的赞赏?阎连科到底是接受了基督教的救赎观, 还是仍然停留在他对“土地”的思索?
二
对于三姓村苦难的核心问题“死亡偏爱三姓村”的解答, 作者在作品第一卷的第十六章用近似于注释的方式介绍到:“8年前耙耧山里曾来过十几个外国人, 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门派往这里对喉堵症高发区的调研人员, ……他们发现环绕三姓村数十里, 除了有甚于高密的无法精确计算的水氟含量外, 空气、土壤、植物中还有一种混合毒素, 这种毒素中可能有126种元素之外的新元素。是什么元素, 却又无力确认。”这种解释可能是出于结构上的考虑, 但这无疑是消解了死亡的普遍意义, 而只将这宿命归于了三姓村。其实, 死亡哪里是只偏爱这三姓村, 整个人类也都受着死亡的奴役, 每个人的一生都伴随着对死亡的惧怕。正如舍勒所说:“死并不处在生命的实际终点, 或者哪怕只是一种以有关其他生灵的经验为基础的对此终点的期盼, 不如说, 作为一切生命要素的重要成分, 死伴随着整个生命。”[2]
这种对死亡的解释显然不同于基督教:在《圣经》中, 死亡是源自人类的始祖犯罪悖逆上帝带来的惩罚, “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 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 因为众人都犯了罪。”[3]这里讲的是“众人都犯了罪”, 也就是说世人都像三姓村的百姓一样, 是被罪所污秽了的人。三姓村里, 司马蓝因为怕死, 就派自己的情人去做“人肉生意” (卖淫) 赚钱为自己治病;村人为了挖灵隐渠, 派年轻的姑娘媳妇去做人肉生意赚钱买工具;蓝百岁与司马蓝的娘偷情;为留住卢主任, 三姓村“光明正大”的找年轻漂亮的姑娘去陪他睡觉……可以说, 这短命的三姓村人时时刻刻离不开的是淫乱的罪。有评论者说, 三姓村人是自强不息的, 不惜一切代价去延长生命, 比如让女人去做“人肉生意”。然而事实真的是这样的吗?司马蓝带领一帮人去教火院卖腿皮, 希望能用赚来的钱买挖渠的工具。但是这些人得了钱之后全都将这些钱归了自己, 岂非单求自己益处的最好“写照”吗?阎连科以及众多的中国作家显然是没有意识到人罪恶的深重, 而只满足于自己“狂欢化”的叙述。没有对罪的敏感, 也就没有了对人性幽暗的负担和忧思, 只能眼巴巴的看着人死去而无能为力。所以, 在阎连科笔下, 四十岁的死亡也只成了三姓村的“专属”, 哪里还知道我们这些“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的人, 也同样受着“死荫幽谷”的挟制。
阎连科在《日光流年》的自序中说:“我……没有陶渊明那样内心深处清美博大的诗境。我想实在一点, 具体一点, 因为今天我们生命的过程就这么实在、具体, 活着就是活着, 死亡就是消失。”[4]这种生命观在《日光流年》中有深刻的体现。是对死亡的恐惧使司马蓝对生命有了更多的思考, 然而, 这些思考与他的“主人”阎连科似乎没有什么区别。司马蓝在儿时就在想:“人还是永永远远的活着好……只要能活着就好。”[5]司马蓝的媳妇竹翠的生活观显然不同于他, 在一次酣畅淋漓的性事后, 竹翠对生命有了更多的体验, 她说:“原来半辈子我都是白活了, 我没有像今夜这么快活过, 浑身骨头都酥了, 我一直以为男女的事, 就是女人侍奉男人让男人醉了就行了, 就完了。今夜我才知道女人也有这么受活的时候哩, 才明白人活着果真是好呢。”[6]在竹翠看来, 人活着乃是能“受活”, “受活”就是人生最大的意义。司马蓝夫妻是三姓村人的代表, 也似乎是国人的代表, 他们对“活着”的看法这么“实在”。
然而, 正如刘小枫所说:“人类存在的秘密并不在于仅仅单纯的活着, 而在于为什么活着”[7]。阎连科虽将生命的实在界定为只要活着就好, 又很矛盾的提出:“这来去之间的人事物镜, 无论多么美好, 其实也不是我们模糊的人生目的。我不想说什么终极的话, 而是想寻找人生原初的意义”, [8]显明作家的意识里, 显然也在寻索着终极的意义, 吃喝拉撒睡显然并不是他所追求的。然而, 《日光流年》中的每一个人物都在追求这样的生活, 拘囿于无法超越的生活观之下。
而作家的另外一部长篇《受活》中, 茅枝婆所带领的一群残缺的人被“完全人”愚弄, 最后回到了受活庄。这受活庄人称自己所生活的土地为“天堂地”, 因为“这里一年四季有吃不完的粮, 日子过的散淡而殷实。在过去和未来的岁月中, 继续种天堂地成了茅枝婆为之奋斗的一个目标, 成为全庄人对美好的一种向往与寄托。”[9]可以看出, 这“天堂地”同样是只关注吃喝拉撒睡, 而非《圣经》中那因上帝而被赋予超越性意义的迦南地或真正的“天堂”。我们可以想见如果三姓村人被治愈了喉症将会怎样生活———毫无疑问, 会是和《受活》里这“天堂地“一样, 延续着缺少了上帝、超越也无从谈起的吃喝拉撒睡的生活。
三
作为乡土观念极重的作家, 阎连科小说的灵魂乃是从生养他的土地而来, 而不是似陀思妥耶夫斯基或者北村那样从《圣经》而来。所以作品中展现出的, 只能是对痛苦的书写, 对世俗生活态度的描述, 和对自我拯救的盼望。但这盼望显然只能流于痛苦再痛苦, 绝望再绝望, 而这没有超越的绝望, 却仍为阎连科所眷恋。学者郜元宝评论说:“阎连科站在传统背景中, 拒绝外来的思想有资格解释这篇亘古不变的土地, 从而拒绝农村题材小说的传统……倘若仅限于拒绝一切思想性话语, 而不在拒绝中产生新思想与新话语, 那么思想和话语的封闭将不可避免”。[10]但这缺乏了超越精神和神性的乡土观念, 缺乏了内在精神的支援, 也必然难以生发出超越的精神。无尽的书写中, 只能是无尽的书写这无尽的绝望。
《拆解与叠拼》[11]文学演讲收入了阎连科21篇演讲, 在这21篇演讲中, 阎连科几乎每篇都会提到卡夫卡、马尔克斯和《百年孤独》。但是, 阎连科显然对卡夫卡不感冒而对《百年孤独》情有独钟。他认为《变形记》“之所以变, 是因为外部环境强烈的催化, 而不是内在关系微妙或强烈的调整”。[12]而当马尔克斯写作《百年孤独》时, “卡夫卡由人为虫的荒诞小说观被他由外部引入到了小说内部, 引入了故事的本身。故事的发展与变化不再依赖外部荒诞环境的催化, 而是仰仗故事内部、内在关系的幻术般的调整”。[13]可以说, 大量经典现代主义外国文学作品的阅读不但帮助阎连科解决了“如何写“的问题, 而且在人性幽暗的揭示和对人类苦难的书写上对阎连科产生了重大的帮助。乡土观念只会显出苦难和其世俗的生活态度, 却缺乏揭示和看见的能力, 而现代主义文学观念的引入恰恰是为阎连科提供了这种能力。
3.死亡病程的书写范文 篇三
关键词:喻世明言;死亡书写;道德教化;劝善
《喻世明言》作为俗文学的优秀之作,其功能正如鲁迅先生所言:“以意度之,则俗文之兴,当由二端,一为娱心,一为劝善,而尤以劝善为大宗。”作为市民日常的娱乐消遣方式之一,《喻世明言》的“娱心”功能不必赘述。而“劝善”功能则是通过描写人物的悲欢离合进而实现直接或间接的道德说教,其中,死亡书写是小说家最常使用的方式之一。道德因素隐含在整个死亡叙事过程中,成为作者构建死亡情节的重要情感指向。
纵观《喻世明言》中的死亡情节,可将其分为四大类:惩罚性死亡、献身性死亡、灾难性死亡和生存性死亡。其中,生存性死亡是一种客观死亡,比如人物因年岁高而老死、病死。这类型的死亡反映的是自然界生命生存的基本法则,并不一定承担特定的旨意,它往往只是构成叙事或抒情的一个环节,或推动情节发展,或表示故事尘埃落定,这类型的死亡书写往往不存在小说家的主观道德褒贬,故而略去不谈。下文将分三个部分,着重探讨惩罚性死亡、献身性死亡和灾难性死亡背后的道德教化。
一、惩罚性死亡
惩罚性死亡是指人物因犯错而遭受来自外部力量的制裁。既有惩罚,则必有受惩方和施惩方,受惩方是指因犯了错误而需要承担的相应责罚的一方,即日常所说的代表“坏”、“恶”的一方,而施惩方则代表了制定规则的评判方,是代表“好”、“善”的一方。小说家通过施惩方的行为和言语来弘扬正义,通过受惩方得到应有惩罚来警示世人,两者的共同目的都是“劝善”。而根据受惩方与施惩方的关系,又可将惩罚性死亡细分为受惩方与施惩方分离的死亡、无明显施惩方的死亡、受惩方与施惩方合一的死亡。
受施分离是惩罚性死亡中数量最多的一类,在《喻世明言》中极为常见,通常表现为作恶多端的坏人受到来自正义力量的制裁。在这类死亡书写中,受惩方与施惩方十分明确且截然分离,受惩方无恶不作,最终受到来自施惩方的严厉制裁。如在第十五卷《史弘肇龙虎君臣会》中,尚衙内见色起意,却“见主人不肯,今日来此掀打”,最后被郭威一刀了结。再如第二十卷《陈从善梅岭失浑家》中的镇山虎杨广,“占据南林村,打家劫舍,杀人放火,百姓遭殃”,最终被陈从善一矛刺于马下,“枭其首级,杀散小喽啰”。小说家通过书写受惩方的死亡,印证“恶有恶报”的朴素道德观,从而达到道德教化的目的。然而在这类故事中,施惩方既可以是人,也可以是人死后的灵魂。比如在第二十四卷《杨思温燕山逢故人》中,韩思厚之妻郑义娘为夫守节而死,韩思厚发誓“我当终身不娶,以报贤妻之德”,然而却因贪恋美色娶了孀妇刘金坛。刘金坛原是冯六承旨之妻,其夫死后,“其妻刘氏发愿,就土星观出家,追荐丈夫”,然而她也违背誓言,花钱还俗后嫁给韩思厚。违背誓言的两人最终被两个鬼魂掷入水中溺死。“一负冯君罹水厄,一亏郑氏丧深渊”,两人的死亡也恰恰说明了“善恶临终总有报,举头三尺有神明”的报应观,这对于听者而言,无异于一场形象生动的道德说教。
无明显施惩方的死亡是指施惩方模糊不清。在这类死亡中,死亡个体虽然也是被惩处而亡,然而施惩方却是隐匿的,施惩方的执行权实际上大多由具有抽象意义的某种道德标准承担。从受惩方的意愿来看,其死亡并非出于主动自愿,而是被迫接受,受惩方无力逃脱死亡的惩罚,小说家的道德教化目的也随之达成。这类死亡在《喻世明言》中多表现为人物突然生病,最后小病致死。如在第一卷《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陈大郎“只图自己一时欢乐,却不顾他人的百年恩义”,设计与蒋兴哥之妻三巧儿偷情,后得知蒋兴哥休了三巧儿,突然受惊害病,“这一惊非小,当夜发寒发热,害起病来。这病又是郁症,又是相思症,也带些怯症,又有些惊症,床上卧了两个多月,翻翻覆覆只是不愈”,最终病死他乡。他的死并非自愿,而是小说家的刻意安排,小说家想借陈大郎之死教化世人“殃祥果报无虚谬”。再如第二十六卷《沈小官一鸟害七命》中的张婆,其丈夫张公谋财害命,张婆见老伴被凌迟而死,“惊得婆儿魂不附体,折身便走。不想被一绊,跌得重了,伤了五脏,回家身死”。张婆虽无害人,但她享用了丈夫杀人得来的不义钱财,故而也遭了报应,正应了说话人在结尾处所说的“积善逢善,积恶逢恶。仔细思量,天地不错”。在这类的故事里,无形的道德准则获得了施惩权力,俨然如一个无所不知、无处不在的神明,作恶者谁也逃脱不了受惩罚的命运,迟早会接受死亡的审判,故而这种死亡书写的道德警示力度也就得以最大化。
受惩方与施惩方合一的死亡是一种自我惩罚式的死亡,该类死亡的施受方为同一个个体,这种惩罚性是向内的、自省式的。要达到施受合一,需要人物有足够的自觉意识,能对自我及其所代表的群体所犯的错误具有足够清醒的认识才能实现。施受合一的死亡,在惩罚自我以表忏悔的同时,也期望以自己的死代替他们所代表的群体,为这个群体谢罪,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死亡是具有献身意味的。在第三卷《新桥市韩五卖春情》中,桑菜园水月寺主持因犯色戒,自尽于羊毛寨,落得一个“久滞幽冥,不得脱离鬼道”的下场。而同样的例子在《月明和尚度柳翠》中也有,玉通禅师自言“自入禅门无挂碍,五十二年心自在。只因一点念头差,犯了如来淫色戒。你使红莲破我戒,我欠红莲一宿债。我身德行被你亏,你家门风还我坏”,后于禅椅上圆寂而死。再如第八卷《吴保安弃家赎友》中的李蒙因不听郭判官的劝谏,一意孤行,使士兵们陷于敌人的埋伏中,后悔羞愧,因而“拔出靴中短刀,自刺其喉而死”。此外还有第二十五卷《晏平仲二桃杀三士》中的田开疆,在公孙接死后,他认为“我等微功而食桃,兄弟功大反不得食”,最终因羞愧而拔剑自刎。由上可知,这种死亡方式的施受双方含混不清,同一个个体承担两种行动,先恶后善,这使得旁观者很難去界定这个个体究竟是属于“善”的范畴还是属于“恶”的范畴,但究其本质,小说家还是期望借这种死亡书写实现导人向善的意图。
纵观惩罚性死亡的三个小类,其区别主要在于施惩方的不同。然而不管是由正义之人执行惩罚,还是由隐匿的道德神明实现因果报复,抑或是由犯错之人自我了结,其共同点都在于,小说家希望借惩罚性死亡告诫世人做恶终有恶报,且这种报应可能是致死的。以世人对死亡的畏惧之心,实现其道德教化的意图。
二、献身性死亡
献身性死亡是基于死亡个体主动奉献生命,献身可以理解为牺牲,献身性死亡可能源于他杀,也可能源于自杀。献身性死亡的自杀与惩罚性死亡中的施受合一的自杀,相似之处在于两者都是自愿死去,但区别在于:前者并无过失,却出于某种为他人奉献的目的而死;而后者是个人犯错后愧疚难当,因而自裁而死。是以,判断是否为献身性死亡有两个原则:一是人物自愿死去,死于谁之手则不必深究;二是死去之人并无道德过失。献身的目的虽然多种多样,但综合而言,大部分是为道义而死。根据献身主体之性别,可将献身性死亡分为男子为义献身的死亡和女子为义献身的死亡。
对于男子而言,“义”多指君子应有的德行,可大致概括为“忠孝仁义礼智信”,而在“三言”中,男子之“义”的最高准是重视朋友义气。因而男子为义献身的死亡,在《喻世明言》中多表现为男子为友而死。比如第七卷《羊角哀舍命全交》中的左伯桃视“义气过于骨肉”,虽然他与羊角哀并非亲生兄弟,但仍在寒冬中将自己身上的衣服和粮食都让予羊角哀,自己冻死于枯桑下。后左伯桃的鬼魂被荆轲与高渐离所扰,遂托梦于羊角哀,羊角哀“宁死为泉下之鬼,力助吾兄,战此强魂……以报吾兄并粮之义”,于是自刎而死。一个将生存的希望留给朋友,舍生求义,一个愿为对方而死,舍身就义,男子之义体现得淋漓尽致,小说家借这两人的献身性死亡来赞颂“古来仁义包天地,只在人心方寸间。二士庙前秋日净,英魂常伴月光寒”。与这个故事类似的还有《范巨卿鸡黍死生交》,张邵在赴试途中遇到重病的范巨卿,张邵认为“大丈夫以义气为重,功名富贵,乃微末尔”,于是放弃应举,照顾范巨卿,并与之结为兄弟。后两人分离,约好明年重阳到张邵家重聚。然而范巨卿因溺身于商贾而忘了一年之约,等他记起时已来不及赶到千里之外的张邵家,但他不愿失信于朋友,于是自刎而死,“人不能行千里,魂能日行千里”,雖然他的身体不能到达,但他的魂魄驾着阴风特来赴鸡黍之约。张邵见到范巨卿的灵魂后,辞别家人前往范巨卿家中,在其尸首前拔刀自刎。“明帝怜其信义深重,两生虽不登第,亦可褒赠,以励后人。范巨卿赠山阳伯,张元伯赠汝南伯。墓前建庙,号‘信义之祠,墓号‘信义之墓”。这些男子之死,正如颜翔林所说的,“人物呈现为一种社会正义性的悲壮意义”。
对于女子来说,“义”多指妇道妇德,它要求女子应当坚守节操,谨守礼节,不做违背妇道之事。因而女子为义献身的死亡,多表现为女子为丈夫守节而死。前文提及《杨思温燕山逢故人》中的郑义娘便是为丈夫守节而死,她的丈夫在逃难中“被缧绁缠身之苦,为虏所掠”,她也被撒八太尉所掳,郑义娘思及“生如苏小卿何荣?死如孟姜女何辱”,于是暗抽裙带自缢梁间,义不受辱。在她看来,自己若贪生,便会侮辱丈夫,因而她为“丈夫守节丧身,死而无怨”。再如《众名姬春风吊柳七》中的妓女谢玉英,虽然她只是柳永的相好之一,然而在柳永死后,“谢玉英便是他亲妻一般”,为他操办丧礼,尔后“不逾两月,谢玉英过哀,得病亦死,附葬于柳墓之傍。亦见玉英贞节,妓家难得”。还有第二卷《陈御史巧勘金钗钿》中的顾阿秀,顾父嫌贫爱富,欲退掉她与鲁学曾自小订下的亲事,阿秀却断然拒绝,她认为“妇人之义,从一而终”,若男方无法下聘,她“情愿守志终身,决不改适”。后顾阿秀被他人所骗,清白被污,她自认愧对鲁学曾,故而自缢而死,后人赞她“死生一诺重干金,谁料好谋祸阱深?三尺红罗报夫主,始知污体不污心”。总的来说,这一类型的女子或是“按照自身的性格逻辑,以死亡的行动达到道德实现的目的”,亦或是遵循小说家意识,实现其创作的道德目的。对于这些女子,小说家明显是持赞扬态度的,或者说,小说家正是借助这些女子的死亡,来传达自己对女子之“义”的阐释,倡导众女子效仿这类献身性死亡。
正如曹文轩所说:“文学不是福音书,文学家常要十分狠心甚至是残忍地处理一些人一些事。为了思想情感上或美学上的效果,小说的绝情常使人寒冷彻骨。”小说家书写这些为义献身之人的死亡,教化后人应当以义为重。这种对死亡的充分肯定,不仅是伦理与正义的崇高,也符合人们的审美期待。
三、灾难性死亡
灾难性死亡是一种由外力导致的死亡,这类死亡的死者在道德上既没有值得赞扬之处,但也没有不当之处,这些人的死亡,或是为了情节的推进,或是为人物的行动作出合理化的演绎。也就是说,这些人的死亡,既不像惩罚性死亡一样,是小说家为了告诫什么,也不像献身性死亡一样,是小说家为了弘扬什么,他们的死亡是“作为叙事艺术的必要结构,它调节整个故事的结构功能,把握叙事节奏和整合事件发展的逻辑行程”。这类型的死亡与前文提及的生存性死亡的区别在于:生存性死亡是纯客观的,不一定承担特定的旨意,而灾难性死亡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承担了创作者的创作意图。只不过这种意图的指向并不是来源于死者,而来源于杀害死者的凶手。总体而言,这类死亡书写有一定的道德教化,但效力相较于前两类死亡更弱一些。根据死亡制造者的不同,可将灾难性死亡分为人为灾难的死亡和环境灾难的死亡。
所谓人为灾难,即指灾难性死亡是人为直接造成的。死者并非因对抗性的争斗,或是因凶手的有意行为而死去,死亡的到来是毫无准备、意料之外的。比如说前文提及的《沈小官一鸟害七命》中,沈秀带着画眉鸟出门,“不想这沈秀一去,死于非命”,被一个见财起意的箍桶老头谋财害命,故事也由此而起,引发了后文六个人的死亡。死亡对沈秀来说是生命的终结,然而对整个叙事艺术来说却是重要的契机,是链接人物关系、情节发展的重要纽带。沈秀不是小说家重点褒扬或批判的对象,他只是一个引子,由他引出后文的种种闹剧,这才是小说家创作的着力点,小说家借沈秀之死,批判了见财起意、屈打成招等恶行,启示人们“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与此类似的还有《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贩珠的主人家老儿,《木绵庵郑虎臣报冤》中的石匠、美姬,《闹阴司司马貌断狱》中的使臣和两樵夫等等。这种灾难性死亡的出现,带来叙事突变,一方面使故事跌宕起伏,另一方面这种无意而为之的死亡,表现出死者的无辜和命运的捉弄,也侧面表现了小说家对凶手的道德批判。
环境灾难的死亡是指灾难性死亡是由时代或环境间接造成的。这类死亡没有特定的凶手,或者说凶手是间接、隐含的,他们对死者没有直接、明显的杀害动机。由环境引起的死亡事件,有两个特点:一是死亡往往呈现为群体性特征,即死亡并非针对特定的个人,而是波及到整个群体;二是造成群体死亡的直接原因虽非明确人物,但追根问底,这样的作品最终隐含的控诉大多数还是指向人类的。在《喻世明言》中,环境带来的灾难性死亡往往体现在战争中。比如在《单符郎全州佳偶》中,邢知县一家,除了春娘一人,其余皆死于战乱。而《杨八老越国奇逢》中的诸多百姓也因倭寇入侵而被杀,而被倭寇俘虏的百姓们也在下次战争中被当做挡箭牌推到交战的最前线。在《葛令公生遣弄珠儿》、《闹阴司司马貌断狱》中也有大量士兵战死。这些死去的人都处于弱势地位,他们面对强大而不可抗拒的环境,反衬出他们生命历程的悲壮感和宿命感。小说家通过这些弱者的群体性死亡,道出了一个时代的无奈与艰难,间接表达了对该时代、环境的批判,尤其是对战争发起者的道德控诉。
不管是人为灾难造成的死亡,还是环境灾难造成的死亡,背后都体现了小说家对无辜受害难者的同情,同时也引发了读者或听众的对死者的悲悯之情,小说家借此间接实现了对死亡制造者的道德谴责。
《喻世明言》凡四十篇,各篇独立,其中不乏纯粹的游戏之作,然蕴涵道德教训的篇章仍是占绝大比重,因果报应之谈几乎无处不在,这也是社会不平的一种曲折表现。人间不平,百姓则寄希望于“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如果不报,时候未到”,借此寻求心理平衡。而小说家顺应这种社会心理,借用死亡书写,通过惩罚性死亡惩处坏人恶事,通过献身性死亡褒扬好人义事,通过灾难性死亡批判使无辜者受难的死亡制造者。既达到取悦听众的效果,也起到导人向善的道德教化功能。就如颜翔林所说:“任何一个杰出作家都必然是运用死亡意象的结构功能的高手。”在《喻世明言》中,也是如此。
注釋:
鲁迅:现代小说史略[M],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66
杨宗红:死亡的神异书写及道德救世——兼论话本小说民间信仰书写之由[J].
梁晓昀:以死亡关照生命[D].广西大学,2012.
冯梦龙编,陈曦钟校注:喻世明言[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4.P247
同上,P327
同上,P327
同上,P423
同上,P425
同上,P427
梁晓昀:以死亡关照生命[D].广西大学,2012.
冯梦龙编,陈曦钟校注:喻世明言[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4.P1
同上,P26
同上,P32
同上,P452
同上,P453
梁晓昀:以死亡关照生命[D].广西大学,2012.
冯梦龙编,陈曦钟校注:喻世明言[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4.P77
同上,P488
同上,P127
同上,P439
同上,P119
同上,P123
同上,P123
同上,P266
同上,P268
同上,P271
颜翔林:死亡美学[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P192
冯梦龙编,陈曦钟校注:喻世明言[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4.P417
同上,P417
同上,P422
同上,P195
同上,P196
同上,P42
同上,P43
同上,P51
颜翔林:死亡美学[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P166
曹文轩:小说门[M],作家出版社,2002年,P22
李爱娟:明代四大奇书评点中的死亡论述[D].广西师范学院,2014.
王玉琴:论文学中的死亡意识[D].南京师范大学,2005.
颜翔林:死亡美学[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P54
梁晓昀:以死亡关照生命[D].广西大学,2012.
冯梦龙编,陈曦钟校注:喻世明言[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4.P443
李爱娟:明代四大奇书评点中的死亡论述[D].广西师范学院,2014.
梁晓昀:以死亡关照生命[D].广西大学,2012.
颜翔林:死亡美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P55
参考文献:
[1]冯梦龙编,陈曦钟校注:喻世明言[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4,10.
[2]曹文轩.小说门[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2,07.
[3]鲁迅.现代小说史略 [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04.
[4]颜翔林.死亡美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08.
[5]王玉琴.论文学中的死亡意识[D].南京师范大学,2005.
[6]梁晓昀.以死亡关照生命[D].广西大学,2012.
[7]李爱娟.明代四大奇书评点中的死亡论述[D].广西师范学院,2014.
【死亡病程的书写范文】推荐阅读:
妇科病例病程记录范文12-03
内科首次病程记录范文03-09
车祸外伤病程记录10-26
白内障病程记录07-16
死亡事故报告范文08-04
死亡证明格式范文01-15
死亡赔偿金协议书范文02-11
死亡的诗句12-02
勇敢面对死亡的名言名句07-08
如何让孩子面对死亡的话题07-04